博文
“他的表现更多是灵性而不是宗教的”——观纪录片《巴斯德》有感
 精选
精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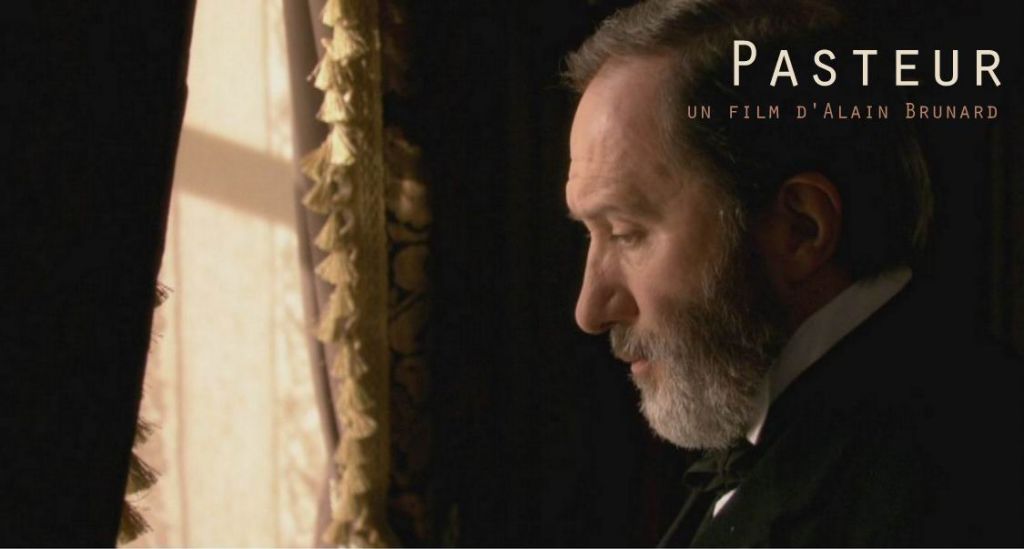
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微生物学奠基人之一路易·巴斯德(1822年12月27日-1895年9月28日)以否定自然发生说、倡导疾病细菌学说和发明预防接种方法而闻名,也是第一个研制出狂犬病和炭疽疫苗的科学家,被世人称颂为“进入科学王国的最完美无缺的人”。然而,1995年,在巴斯德逝世百年纪念之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史教授拉尔德·盖森出版了《巴斯德的隐秘科学》一书。书中声称,巴斯德这位“最完美无缺的科学家”有欺骗行为,巴斯德的实验记录有的不符合他公开的说法,而且他还从事了违反医学伦理的试验。《纽约时报》当即报道了该书的出版,而196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佩鲁茨则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为先驱辩护》,对拉尔德·盖森的说法进行了详细的反驳。此后,相关争论一直不断。
近日,在由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和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联合在上海举办的“法国,科学的形象”纪录片展映中,纪录片《巴斯德》面向中国公众,回顾了巴斯德这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学巨人的生平,特别是科学史上那段颇具争议的往事。其中固然不乏名利的争夺、科学的欺骗、庸众的误解——所有在今天的科学界依然掺杂的不纯粹因素,然而,真正的科学家身上依然让人看到动人的人道关怀和对于科学自身原则柔韧而顽强的坚持。片中传达的许多关于科学如何走向公众的理念在今日也依然值得引起科学界的思考和讨论。
什么是科学精神?
早先,巴斯德只是个化学家,还不是个医生,但他已经开始在狗身上做实验了。1865年在巴黎,彼德医生在公开场合反对他说:“微生物的发现对医学没有多大意义。”巴斯德则反驳:“不承认微生物的重要性,意味着杀死病人的不是无知而是愚蠢。”当时,相信他研究的人少之又少,只有一个医生——米尔·胡跟随他。巴斯德对他的同伴说:“医学绝对是个重要领域,不能只留给医生。”但即使是米尔·胡,也忐忑地劝阻他说:“今天就尝试在人身上接种疫苗,意味着冒害死他的风险。”对此,巴斯德的反应是:“我不是医生,请别叫我医生。我只是接受自己所做研究的引领。”
一天,有个两天前被狂犬咬伤的乡村孩子约瑟芬·美斯特由母亲带着来找正在研制狂犬疫苗的巴斯德求助。巴斯德对孩子的母亲说:“14个咬破处,14个可供病毒进入的通道。病毒可能已经向孩子的大脑扩散了!我不能保证这个方法对您的孩子一定有效。”但约瑟芬的母亲坚持:“还是请您试一下吧,您不试他也会被狂犬病夺走生命的。”
由此,在一个极为隐秘之处,人类开始了第一个疫苗接种方案。巴斯德给小约瑟芬注射的产品发挥作用的速度超过了病毒扩散的速度,防止了病毒扩散到大脑。约瑟芬的母亲这时才问:“巴斯德先生,这是个什么产品?”但巴斯德怎敢告诉她:这是狂犬病病毒,他尝试了以毒攻毒?他将这次的成功归于偶然。
又有一天,米尔·胡医生给母鸡注射剧毒性菌株,母鸡安然无恙。他把这事告诉巴斯德,巴斯德问他:“你确定菌株是有效吗?”医生想了想,说:“可能是休假时忘了,我去把它扔掉。” 巴斯德却说:“等等,给母鸡再注射一剂剧毒性菌株,以确定你是不是碰到了世界上抵抗力最强的母鸡。”
在治疗约瑟芬的过程中,米尔·胡数次提出:“把孩子当试验品是不道德的,我们不知道应该用在人身上的剂量。”巴斯德的回答则是:“我确定我是在救一个孩子的命,而不是在试验我的疫苗。”但他的内心也困惑了:1865年9月11日,他两岁的女儿卡米尔因肝肿瘤夭折,上帝无能为力。他其余的4个孩子最后也只活下来两个。当时他自责:“如果我是医生,不是化学家,我就能救他们了。”自那以后,他把自己当作追捕隐形生物的猎人,显微镜就是他的猎枪。但对于一个别人的孩子,他有权力用一套自己还不是百分之百有把握的方法去拯救吗?他为小约瑟芬彻夜难眠,怕自己害了他,甚至在回家乡阿尔布瓦休息前,还叮嘱小约瑟芬每天写信告诉他发生的事。15天假期里,医生的家里连续不断地收到病人汇报情况的信件。
巴斯德在陋室的葡萄酒里发现了微生物,破解了发酵的谜团,又在变质的黄油里发现细菌。这些发现把巴斯德引上了治疗传染病的道路。他死后,人们困惑他如何用那个年代里的显微镜看到了那些“小东西”。事实是:他在观察,也在推理,想象力总能把他带往正确的方向。比如狂犬病毒,巴斯德徒劳找了几个月,没法找到它——只有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到它,但那要在一个世纪后才被发明。可巴斯德高于普通人的执着,使他转向他认为病毒毒性比狗小的兔子,试图从兔子的脊髓里找到病毒。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小约瑟芬对打针充满恐惧的时候,巴斯德带他去实验室,用显微镜比较各种细菌。1878年,炭疽病肆虐时,羊群相继死去,农人以为土地受了诅咒,但相邻田地上的羊群却活得好好的。当时有研究人员试过用感染病毒的干草喂羊,可是没用,病毒看起来不是被吃进羊肚子里的。巴斯德又带着小约瑟芬重回现场,发现是蓟割破了羊的嘴,病毒由伤口进入血液传染给羊。经过观察,他们又发现,是蚯蚓将细菌从地下带到地上,并使之附着到新的有机体上。这些都使小约瑟芬懂得了治疗的意义,并从中学到了“观察—对比—假设—证明”的科学方法。长大后,约瑟芬·美斯特成为了巴斯德研究所的警卫,并在各种舆论的热议中,成为巴斯德坚定的精神支持者和巴斯德研究项目的捐款人之一。而即使是其他一些生命垂危的病人,也在临终前用无声的语言向医生的治疗努力表达谢意,支持医生“为了更多的病人”。
今天,当医生和病人互不信任,互相抱怨指责时,巴斯德、约瑟芬以及约瑟芬的母亲,他们对于彼此的理解、尊重、责任意识和对于未知事物的科学态度,也许已给出了一条舒缓医患矛盾的人文幽径。
科学需要怎样的传播者?
作为一个有远见的人,巴斯德注定要与绝大多数人作战。在研究所内部,他关于微生物和疫苗的观点屡次受到众人的质疑。很长时间里,除了太太玛丽(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校长洛朗的女儿)的信任和鼓励,巴斯德几乎孤单一人且一无所有,终日在阁楼里与老鼠相伴着做实验。长年待在实验室里的巴斯德没有注意到,当时的法兰西共和国已形成一股新的力量——新闻媒体。在狂犬疫苗治疗约瑟芬成功后,玛丽建议巴斯德:“现在不要公开约瑟芬的事,这样他们会嫉恨你。你要找合适的时机,结合热点新闻,简洁地向人民而不是向研究所宣布。人民会影响医生。但报告太长太细致了,读者会烦的。快讲朱比尔的事。(那些天,报上正宣传年轻的英雄朱比尔勇救5个孩子于狂犬之口的故事。)”即使从今天的标准来看,玛丽也是一位出色的科技传播者。她有一句幽默的口头禅:“你得承认,按照女人的逻辑总能达到目的。”
一个成功接种的小男孩、一个少年英雄,正当巴斯德团队胜券在握的时候,一直与巴斯德并肩作战的米尔·胡医生却不愿为实验报告签字,认为报告数字造假。这时,巴斯德对米尔·胡医生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有一天你会相信某些事。唯一需要诚实的地方,是在这个实验室里。而在外面,需要遵循其他原则。在科学界,如果不被人接受,再伟大的发现都一文不值。”为此,巴斯德违背了一次原则。他绘声绘色地向公众描述了朱比尔救几个孩子于疯狗之口的过程,以此说服了医生们。报纸则扩大了狂犬疫苗的影响力,人们争相带被狗咬伤的病人来接种。4个月里,共有350人接种,证实了巴斯德的方法。事后,米尔·胡医生对巴斯德说:“其实我一直相信的,可是伦理道德上,我无法选择。”
狂犬疫苗推广后,有一个小男孩的父亲声称他的孩子被巴斯德的疫苗杀死。真相就藏在那个孩子的延髓里。米尔·胡医生给两只兔子注射了死去孩子延髓的提取物,以求证孩子不是死于狂犬病。纪录片在此处略过了验证的结果,镜头直接切换到另一天,使用试验性狂犬疫苗的两个孩子中有一个死了,巴斯德受到巨大责难。米尔·胡医生和另一位医生为巴斯德作证说,孩子死于肾功能衰竭而不是狂犬病。众人指责他们为巴斯德掩饰。
之后,米尔·胡医生与巴斯德之间又发生了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医生说:“如果疫苗受到质疑,医学将退后20年,我们的研究也会。我们离治白喉的药只差一点点了。今天,两个孩子中有一个死了,二分之一。”巴斯德问:“我们要为科学的进步撒谎吗?如果孩子死于狂犬病你会怎么做?”米尔·胡医生说:“我绝不会做我没有百分之百把握的事。”——在疫苗和孩子的死因之间,米尔·胡医生把信心押给了疫苗。
可以说,在与疾病和环境艰难而坚定地抗争的一生中,巴斯德幸运地遇上了能够真切地理解他的爱人和朋友。正如索邦大学在庆祝他70岁生日时所献上的贺词:“不要被无聊的流言阻挠了脚步,请享受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安静的时光。无论自己的努力是否被生活眷顾,你都应该能够在临终的时候说:我尽力了。”是的,他尽力了,并且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作出了符合自己道德良心的抉择。
在维基百科关于巴斯德的词条里,有一段他的外孙路易斯·巴斯德·瓦莱里-拉多对他的评价:“巴斯德仅仅相信天主教中的灵性,但没有参加过日常的宗教活动。尽管巴斯德信仰上帝,但一般说来,他的观点更接近自由思想家而不是天主教,他的表现更多是灵性的而不是宗教的。巴斯德也反对将科学和宗教混为一谈。”将这段话与纪录片《巴斯德》相结合,我们似乎得以理解:一个人何以在顽强的执着中保留适当变通的灵性。这在专注于专业研究的科学界是并不多见的一种能力,某种程度上,我将之视为一个战略科学家所需要的重要能力。
附:
施特劳斯的弟子朗佩特说:哲人必须说谎,当然是指高贵的、必要的谎言。因为哲人知道致命的真相:变易和生成主导一切,所有的概念、类型、种类都是变动不居的。柏拉图是第一个发现这个真相的人,但他没有把这个真相告诉民众。“社会能不能建立在哲人所知道的真理基础上?”柏拉图是第一个敢于这样质疑的哲人,尼采的柏拉图断定:不能。
https://m.sciencenet.cn/blog-1341506-814346.html
上一篇:驱鬼
下一篇:一个更加有趣或更加无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