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转载]皮国立《中医抗菌史》文选(17):西方的营养、中国的禁忌
||| |
以具体的食品而论,牛奶在西人的热病调养,甚至是多数疾病的调养中,可说是占了关键的地位。丁福保在引介日本医学界对伤寒的调养知识时,也强调“食物之摄生”,包括喝牛乳、粥、果汁等流质食物。[1]虽然牛乳在其中,但它却是个问题食物,晚清传教士就曾记载:“若你建议给病人喝些更可口更有营养的牛奶,就会有人提醒你,牛奶属于热性,喝了它会助长病人身体中的火气。由于中国人非常相信那些能够给身体带来健康的食物,在吃了之后会引起致命的后果,因此许多人慢慢地饥饿致死了。”[2]在外国传教士的眼中,中国人以“饥饿”二字调养,甚至不肯喝牛奶,真是自取灭亡的怪异举动。反观西医认为:“伤寒菌在牛乳中最能繁殖,故不洁净之牛乳中,常有病原微生物在内,其他夏秋之交,饮食物中多有种种微生物,偶不谨慎,即能害人。”[3]如果能够去除病菌,倒没有食物寒热的疑虑。又如在20世纪初的美国,甚至有人担心结核菌污染牛奶和牛肉,如何排除食物中的细菌,是当时西方社会较注意的事情。[4]
其实,牛奶未必为中国病人所害怕,因为在温病的调养中,牛奶本来就是一种很好的亦食亦药的物品。如《温病条辨》载:“温病愈后,或一月,至一年,面微赤,脉数,暮热,常思饮,不欲食者,五汁饮主之,牛乳饮亦主之。”[5]又有谓“人乳为补血神品”者[6],对乳类饮品大加肯定,在补养与房中文化中皆可见其踪迹。[7]不过,陈存仁则对“牛奶”用以调养热病的想法不以为然,虽然他在吸收西方营养学知识后,在“饿为忌进食物之意”的前提下,加上了“营养依料则不忌”的补充说明[8],指出流质的营养剂可以被拿来应用在热病调养上,但其对牛奶仍存有疑虑,他说:“伤寒发热期内,不惯饮牛奶者,不可饮牛奶,此为鄙人郑重提出之重大要点。夫伤寒期内,不饮牛奶,此言一出,必将引起整个西医界反对,其实此言确具至理。”陈引著名西医周宗畸有关伤寒不赞成吃牛奶之论文(《民生医药》杂志第31期),来佐证他的见解。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的重点并不是说伤寒调养不能喝牛奶。周举出“近来西方学者曾把发热病人分为两组,一组有丰富的滋养料供给,另一组只有清淡的东西供给。结果两组在痊愈的经过上没有明显的相差”[9],该实验证实,饮食的精粗并不会对热病之调养产生任何差异,牛奶当然可以饮用。虽然陈仍怀疑喝牛奶可能为导致伤寒调养时肠出血的元凶,但他最终把喝牛奶“不适合热病病人”的真实原因归纳为中国病人的饮食习惯与西方之牛奶不合,而非食物(牛奶)本身有问题。他说:
当我做大学医科的学生时,外国老师常常说发热的时候,身体的消耗增加,苟不用滋养料去调济,或将不堪支持。这一说,说得入情入理,颇觉动听。于是遇到发热的病人,就吩咐他睡睡,吃吃牛奶,结果怎么样呢?十个之中,倒有九个病人愁眉苦脸的,很善意地拒绝继续吃牛奶了。我当时心中不免说了一声,好不受抬举。等到我自己抬举我自己的时候(即自己有病),才知道硬抬的风味真类绑票,怪不得人家不惯,我也不惯。于是当仁不让,不能再服从老师的话,不得不把本位化的粥汤清茶代替了牛奶。[10]
所以,这位医师并不只是觉得应该严守食禁的规范,还建议病人所吃的食物,合于中国人口味。牛奶并非真的对伤寒后的调养无益,而是许多人喝不惯牛奶,才不利于病情。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糖”,由于糖在古典医学的汤液中已经广泛利用,所以当西医说葡糖糖对热病有滋养功用时,中医就颇能接受,例如杨则民谓:“中医药物一部分采诸食疗,而食物之最为人所嗜者,莫若糖味。……前时西医视糖为矫味剂,而不作治疗剂,自葡萄糖疗法发明后,对此忽重视之,普通解热剂中、内服、注射亦每每加糖剂与之,此本中医治疗法也。糖剂不经复杂消化过程即可补给身体,此已为今日营养学者所明了。”[11]在治疗的意义上,张仲景与叶天士都注意到甘味剂的作用,这些都和西医的葡萄糖疗法相同;糖质富含润滑作用,可以减轻刺激,缓解炎症疼痛之刺激;最后就是对病后调理的“健胃”价值,这一点尤为温病学家所重视,杨也加以科学之解释:“热病以后,或胃病日久以后,胃口每不振作,古人称此不曰胃阴虚,即曰肝火盛,此固难测之词。由今言之,实为胃力不足,胃酸缺乏之故,胃力不足最忌用刺激药,叶天士创为甘淡养胃之论,主用沙参、麦冬、花粉、米仁、山药、甘草之属,此类药物含有糖质及淀粉,浓煎内服,可以不经消化而补身体,使胃力休息而日渐恢复,此固恢复胃力之好方法也。”具有淀粉等糖质之药,或如叶天士之“甘酸化阴之剂”,如乌梅、白芍、生地等,都可补充热病后缺乏胃酸所导致的消化力虚弱的问题,此即寻求食物性味的科学证据。[12]自清末以来出现的各种“果子糖汁”,即取糖汁之补血、健脾开胃、润肠之功能[13];民国之后则更多卫生果汁之广告,这类饮品和中国医学理论的冲突较少,而多了汇通之面向。[14]
冲突的一面,即前文初步论及之古典食忌理论中之禁“肉食”,在近代所引发的诸多讨论。裘庆元曾指出肉类对热病调养之害,一则医案记载:“何梅之甥某,热病后转虚,纳少,余曰胃虚,西医亦曰胃虚,入院调理,许一月痊愈,日饮以鸡汁、牛肉汁,余闻之曰殆矣,虚在胃阴而不在胃阳,易以猪肉汁、鸭汁则善矣。未一月,热复炽而殁。”[15]此医案之病患明显地是被西医“补”坏了,食物的寒热属性,本非西医着重之理论。中医曹炳章则提出要多吃凉性食物,肉宜少吃,但可以海产来替代,还不能吸烟,因为“烟含有毒质,助长毒火上焰,能变坏血液与脑神经故耳”[16]。此句话受西医形质化(器官)身体观的影响甚大,但食物宜忌的规范基本仍是传统中医的理论,特别是多吃凉性食物,似为热病食疗的重要准则。[17]李鸿章则谓肉食有毒:“终年饱食肉类,血肉蕴毒既多,一日为外症或传染症所侵袭,则轻症变为重症而死。”[18]可见食肉与外感重病的关系密切。杨则民则指出“西瓜”之功效,并将之与中药“石膏”比较,皆有退热之效。[19]他指出,包括生地、麦冬、芦根、石斛、西瓜、花粉等甘寒养阴的药食,都含有清凉解热的作用,这是它们受温病学者青睐的原因。[20]
另一反面的例子,对牛奶提出质疑的陈存仁却说:“(伤寒)病后忌口不以荤素为别,易消化而有补力者,虽荤不忌;难消化而无补力者,虽素亦不可食。且病后胃口薄弱,一时不可即服补药,因补药呆胃,服药过多,流弊滋生,补身反足害身。鸡汁、牛肉汁补而不腻,味极鲜腴,不但为病人所喜,尤无补药之流弊。”[21]陈反而认为这些肉汁比一些补药更适宜用来做热病后的调养。其论凸显一个问题:热病调养禁食过多肉类,那么喝肉汁可行吗?
晚清以来,市面上已经出现相当多肉类的营养制剂。例如“三星牌黄雌童鸡汁”,广告力陈西医以鸡汁补病人虚弱身体之功,并言“鸡能动风一说,实为无稽之谈”[22],还顺便回应了中医担忧热补的疑虑。而另一则中法大药房的“地球牌牛肉汁”,广告指出人类本来就是由血肉组成,所以用血肉制成的营养品来滋补,一定比传统中药由草根树皮来补身体更加有疗效。该药房还兼售另几种牛肉汁,甚至有牛、鸡混合者,皆避谈传统中医的食禁知识。[23]或者如“三星牌滋补鹿肉汁”,功效为“大补血肉”,但药商也深知中国人惧怕的是什么,这时他们常运用的方式为:强调西医已用科学的提炼法来制汁,所以并没有传统本草文献中所记载的禁忌,诸如鹿肉“过热不可多食”或“少年忌食”。换句话说,鹿肉汁是一项新的、科学化后的商品,和传统的鹿肉有所不同。[24]
民国时出现了更多由肉品制成的更精致的“牛肉精”、“鸡精”等滋补饮料。例如由德国玛尔大药厂制造的“狮力牌”牛肉汁与鸡汁(见图15)[25],就强调蛋白质是人体的营养要素,当然也融入中国“补”的元素,说明该药可以“助消化、抵抗病魔、培本固元”。广告还利用名人服用经验,说明该肉汁的效果卓著。一是举褚民宜,一举爱迪生,前者就不用谈了,虽贵为国民党要员,早岁赴德国学医,取得一纸专门研究兔子交配的博士学位,最后当了汉奸,被枪毙了。[26]至于后者,则为著名之发明家,该广告引述报导指出,爱迪生每日早晨都要喝该肉汁,难怪思绪清晰、创造力无穷。其实究言之,该药顶多和今日鸡精类似而已,这些药物其实凸显了中国人追求“补”身以治百病的思想,在卫生文化的脉络中,被一再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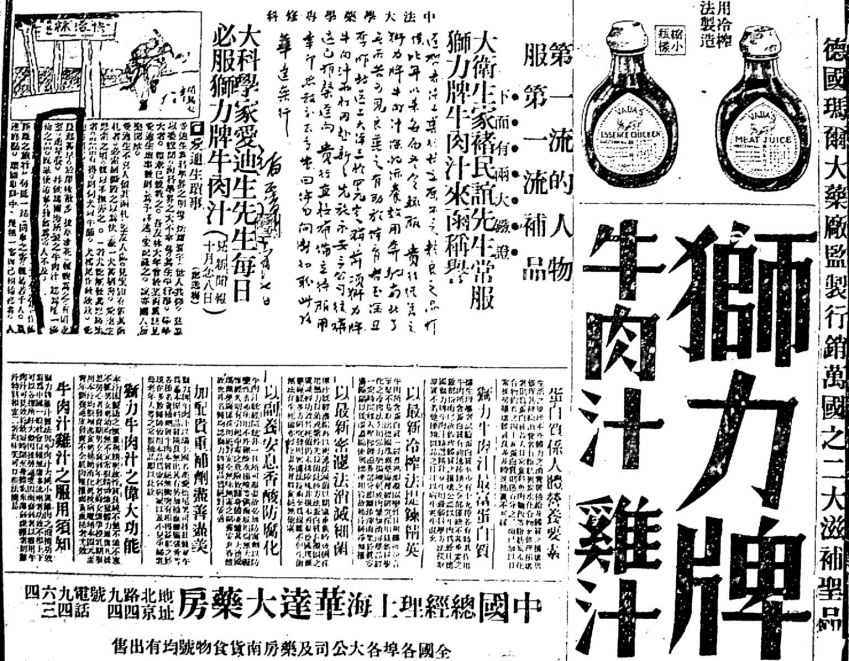
图15 狮力牌牛肉汁、鸡汁
由于古代并无这些补养剂,中医们的讨论往往呈现了不同的两极化反应。吴锡璜言:“西人治毒热,亦有用鸡汤、牛羊肉汁诸补身之品,滋养脏真,静候解热,与我国养正托邪用法,大旨相同。”[27]这是较为肯定西式滋补剂的一面。但他也举例说:“丁巳之秋,鼓浪屿某氏妇病营热,延某国西医能操中国音者诊视。病已十余天矣,某国西医用铁酒、金鸡纳霜、牛肉汁等,谓须补身至四礼拜,方可望愈。余至曰:此用我国医法,可以数日而愈者。投以减味复脉汤加知母,三日痊愈。”[28]他认为用中医的方法治疗,仍有优势,不一定要用西方的调补法。又如徐仁甫谓:“伤寒病勿食实质之物,积滞肠胃,所谓饥不死伤寒,使腹中常饥,食以流动质,如牛肉汁、藕粉、薯芋、芥菜、河口丝。”[29]也同样肯定流质的补养食品,可谓与古典医学理论似相反,又有相互补充之处;或谓有条件的食肉汤:“病患如已食饭多日,行动自如,方可随宜恒食。”[30]
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肉食不利于热病之调养,即便熬成汤汁或饮料也不能接受。陈果夫说,有一位朋友患了伤寒,发烧至102度(笔者按:指华氏度),送到医院后,升高至105度,医生也弄得莫名其妙,后来研究了半天,才知道是医院给病人喝了鸡汤,后来停止喝鸡汤后,热度果然下降。陈说:“中国相传鸡是鲜发的东西,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他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有不少医生,只知其药有效,而不知某种食物对于某药之有害,常识不够,哪能不误事呢!”[31]这也可以用来比较中西医在热病之饮食调养方面的差异,西医认为罹患热病,需要的是补充食物之营养,故谓:“吾人若营养不良,抵抗力减弱,血液中之杀菌素较薄,病毒之感染自易。故传染病流行时,营养宜大加注意,可增强血液中之杀菌素,以防病毒之传染。”[32]但中医则认为罹患热病要守住“饿”,尽量食用清淡的食物,甚至以不食、禁食来应对。其实在热病调养期间,中医对肉食的定义有时也不尽严格,虽不吃是对的,但戴天章谓:“凡温热病新瘥后,但得食糜粥,宁少食令饥,慎勿饱,不得他有所食,虽思之,勿与之也。引日转久,可渐食羊肉白糜若羹汁,雉、兔、鹿肉不可食,猪、狗肉亦然。”[33]多数的肉虽不能食,但也不到谈“肉”色变的程度,或可吃类似碎肉汤的滋补品。故有些中医对这些可以强身的新式滋补品怀有好感,如谈及伤寒之“病后摄养期”时,陈存仁说:
病后总以富于营养、易于消化之流汁为最宜,故伤寒病后,鸡汁、牛肉汁虽属荤品,实为不可缺少之养身妙品也。有若干病家以为病后不宜遽食荤性发食,鸡汁、牛肉汁误为发物,初时颇不敢食,其实此种观念实属大误。盖伤寒非外科病,病后忌口并不忌荤,更不忌鸡。此时需要流汁补品,牛肉汁、鸡汁为唯一适宜之品,此外确无更好更有效力之食品。患病一个月者,需饮牛汁、鸡汁二个月;患病一月半者,需饮汁三个月,恢复元气,充实体力,增进气血,皆属显而易见者。[34]
陈存仁的看法就很明显地与上述陈果夫的疾病体会很不同,前者主张可以用这些肉汁来补身,不应该在“肉”这个禁忌上打转,而是应该着眼肉汁的好消化与不滋腻,适合病人口感,这倒与“临病人问所便”有所类似了。民国以来的“补品”文化的多元发展,其实已经让古典医学的某些“禁忌”松动了,前述肉食的规范即为显例。不少中医已提出了与古典医学相对之概念,引导我们思考汇通两种知识体系的可能角度。
[1] 宫本叔原著,丁福保译:《第一篇·伤寒初步》,《新伤寒论》,第11页。
[2] 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第197页。
[3] 余云岫:《微生物》,第38页。
[4] 彭琼斯撰,陈兆熙译:《微生物与人生》(1931原著),第92—93页。
[5] (清)吴瑭:《温病条辨》,收入李刘坤主编:《吴鞠通医学全书》,第84页。
[6] 何廉臣编著,王致谱等编辑:《增订通俗伤寒论》,第496页。
[7] 郑金生:《药林外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5年,第157—158页。
[8] 陈存仁:《通俗医话》,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医话分册》,第1012页。
[9] 陈存仁:《通俗医话》,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医话分册》,第1020页。
[10] 陈存仁:《通俗医话》,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医话分册》,第1019—1020页。
[11] 附载省略原文:“中医之糖疗法最早施用者为仲景,如甘麦大枣也、小建中汤也、炙甘草汤也,皆以糖为主剂者也。近世之应用最精者为叶天士,如甘酸化阴也、辛甘理阳也、甘润润燥也,皆以糖为主疗者也。”引自杨则民:《(十)论糖质剂》,《潜庵医话》,第185—186页。
[12] 杨则民:《(十)论糖质剂》,《潜庵医话》,第186—187页。
[13] 环球社编辑部主编:《图画日报》第7册,第12页。
[14] 上海申报馆编辑:《申报》,1936年8月7日,第3张。
[15] 裘庆元主编:《慎重性命者鉴》,《医话集腋》,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医话分册》,第359页 。
[16] 曹炳章言:“凡秋瘟病发之时,无病人,宜常食生萝卜、雅梨等凉化之物,然亦不可过量。食物宜多吃植物品,如荸荠、甘蔗、绿豆、鞭笋、菠菜、蒿菜、菘菜(即白菜);少食动物品,如猪、羊、牛、鸡、鹅、鸭、鱼、虾、蟹,及一切油腻之食物;如动物之亦有可食者,如咸蛋、海蜇、海带、海、鲫鱼、土鱼等。宜戒吸纸烟及水旱烟,因各烟含有毒质。” 引自氏著:《第七章:秋瘟之预防》,《秋瘟证治要略》,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温病分册》,第772页。
[17] 陈果夫也说:“喉痛(白喉)如果不十分厉害的,只要大便通畅,多饮盐汤,多吃青菜萝卜生梨等清凉的东西,即可减轻或竟痊愈。” 出自氏著:《卫生之道》,收入陈果夫先生奖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编:《陈果夫先生医药卫生思想遗著选辑》,第155页。
[18] 襟霞阁主编:《致四弟》,《李鸿章家书》,《清代名人家书》下册,第854页。
[19] 例如杨则民谓:“体温持续增高,至如近人所谓,稽留性热者,多现渴饮大汗,神识昏迷状态,此《伤寒论》所谓阳明胃热。用石膏或西瓜,每奏奇效,此病炎暑时常见之,兹录袁之才自记医案一则以征之:丙子九月,余患暑疟,早饮吕医药,至日旰,忽呕逆,头眩不止,家慈抱余起坐,觉血气自胸偾起,性命在呼吸间。忽有同征友赵藜村来访,家人以疾辞。曰:‘我解医理。’乃延入诊脉看方,笑曰:‘容易。’命速买石膏加他药投之。余甫饮一勺,如以千钧之石,将胃肠压下,血气全消。未半盂,沉沉睡去,额上微汗,朦胧中闻家慈叹曰:‘岂非仙丹乎?’睡须臾醒,君犹在坐,问思西瓜否?曰:‘想甚。’即命买瓜,曰:‘凭君尽量,我去矣。’食片许,如醍醐灌顶,头目为轻。晚便食粥。次日来,曰:‘君所患者,阳明经疟也。吕医误认太阳经,以升麻、羌活二味升提之,将君妄血逆流而上,惟白虎汤可治。然亦危矣!’” 引自氏著:《(三十四)石膏西瓜退热之伟效》,《潜庵医话》,第234页。
[20] 杨则民:《(十)论糖质剂》,《潜庵医话》,第186页。
[21] 陈存仁:《通俗医话》,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医话分册》,第1022页。
[22] 环球社编辑部主编:《图画日报》第3册,第71页。
[23] 环球社编辑部主编:《图画日报》第6册,第36页。
[24] 环球社编辑部主编:《图画日报》第5册,第6页。
[25] 上海申报馆编辑:《申报》,1936年9月30日,头版广告。
[26]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76页。
[27] 吴锡璜:《绪言》,《中西温热串解》,第6页。
[28] 吴锡璜:《绪言》,《中西温热串解》,第5页。
[29] 徐仁甫:《实用医学讲义》,第188—189页。
[30] 如谓:“鳇鲟鳔、线鱼胶(同猪蹄、燕窝、海参,或鸡、鸭,荤中煮烂、饮汁更佳),填精益髓;凤头白鸭、乌骨白鸡,补阴除热;猪肺蘸白芨末,保肺止血。以上诸物,病患如已食饭多日,行动自如,方可随宜恒食。此食补方法之大要也。” 引自何廉臣编著,王致谱等编辑:《增订通俗伤寒论》,第496页。
[31] 陈果夫:《六十一、不可轻信亦不可以完全不信》,《医政漫谈初编》,收入陈果夫先生奖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编:《陈果夫先生医药卫生思想遗著选辑》,第241—242页。
[32] 邱峻:《豫防传染病概说》,《社会医报》第190期(1933),第51页。
[33] 戴天章原著,何廉臣重订:《第一卷·温热总论·论温热本症疗法》,《重订广温热论》,第37页。
[34] 陈存仁:《通俗医话》,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医话分册》,第1022页。
https://m.sciencenet.cn/blog-279293-1229496.html
上一篇:[转载]皮国立《中医抗菌史》文选(16):中西医汇通下的疾病观
下一篇:[转载]皮国立《中医抗菌史》文选(18):贡献与局限